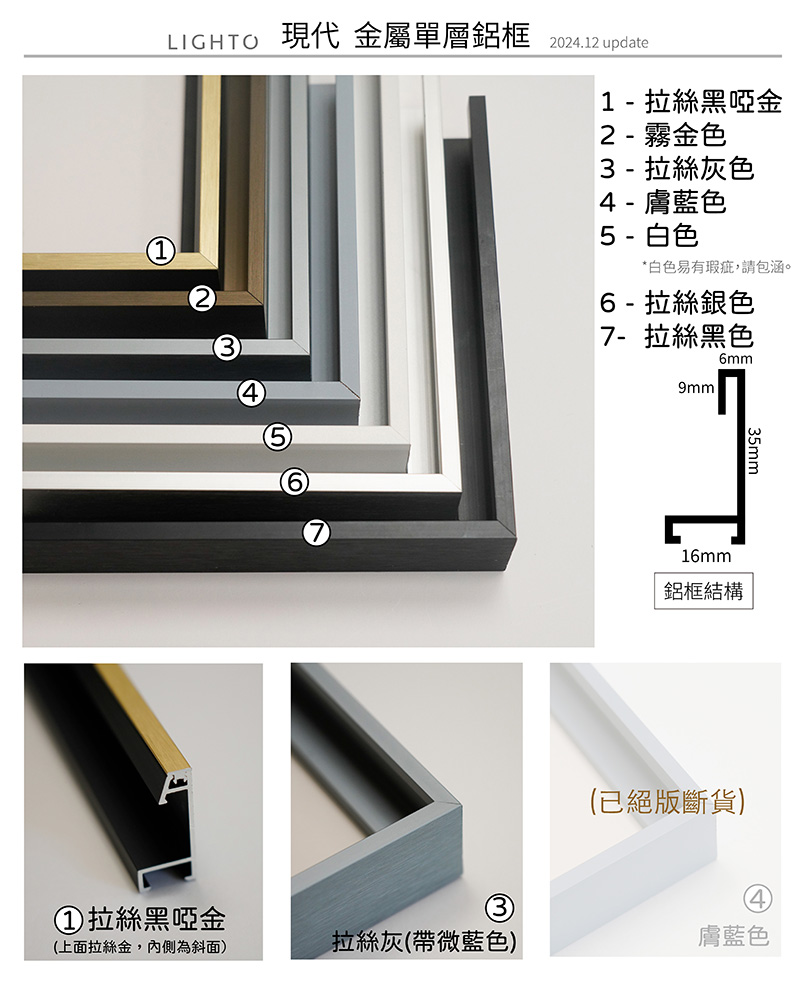--- 輸出相紙: 藝術微噴 雪面藝術紙
*單買相紙:3-5個工作日出貨。
*裱褙工法耗時費工,訂單需等候 2-3週,請耐心等候。
懸掛方式:
鋁框背面均有鋼索,可於牆上黏貼3M無痕掛勾(請購買5kg以上版本以策安全)即可懸掛。
- 作品名稱 / 壁畫 I,壁畫 II,壁畫 III Mural I, Mural II, Mural III
販售作品尺寸:90 x 60 cm
作品年代:1933
米羅為Mural I-II-III畫了由三個畫布部分組成的畫作,這是他特別指定的首批作品,是在完成了一系列基於拼貼的十八幅大型作品(Dupin,編號415-432)之後完成的。這些畫作共同標誌著米羅重新投入繪畫布面的承諾,此前的1928年至1931年間,藝術家曾展開一場旨在「暗殺繪畫」的運動。當時,他考慮放棄所有受尊崇的油畫慣例,轉而創作粗糙、顛覆性的拼貼和由基礎、無足輕重的材料製成的繪畫物件,雅克·杜邦描述為「對『繪畫-繪畫』和理想美的毒箭」(同上,2012年,第152頁)。儘管這種具有挑釁性的虛無主義衝動,但米羅並未完全破壞繪畫的傳統觀念,實際上是在擴展可行的形式潛能,同時進一步擴大了現代藝術中內容的包容性。Mural I-II-III正是這種繪畫與反繪畫之間競爭的直接結果,轉化為米羅迄今為止構思的一些最直接和集中的塑形形式。
Mural畫布三件套是專門為米羅的巴黎經銷商皮埃爾·洛埃布的家中的育嬰室而繪製的。米羅在考慮到這個環境的情況下,選擇了他認為適合兒童世界的圖像和動作敘事,反映了年輕想像力的運作。實際上,米羅的許多圖像中已經顯現出的原始、兒童般的特質使他成為這個項目的理想藝術家。他在這些畫板上組合了幽靈般的人物、滑稽怪異的生物和一隻大鳥。它們參與了追逐場景——在夢中經常出現的情景,也是兒童遊戲和幻想的素材——在每幅作品中從左到右展開。米羅將他的主題置於模糊的藍色夢境背景中,其中包含自然形式的元素——彩虹、海浪、山、被遮蔽的太陽、星星、一輪弯月,其顶端爆发出一顆星星。
米羅在這些畫板上設計的夜間冒險似乎按照Mural III、II和I的順序進行,從左到右。III中的飛鳥和奔跑的人物開啟了夢境;畫布I描述了夜晚旅程的結束和事件序列中的最終轉變——一個人物朝著一個矩形的門戶奔跑,分隔了夜晚的深藍色與白色耀眼的日光,象徵著從夜晚夢境的世界進入日常現實世界的過渡。
米羅對於為兒童創作藝術或關於兒童的興趣可能源於他最近對舞蹈劇場的涉足,這是他在這個領域的首次嘗試。1932年,藝術家受到蒙特卡洛俄羅斯芭蕾舞團的委託,設計了一個芭蕾舞劇的服裝、幕布和舞台設計,搭配喬治·比才的管弦樂組曲《兒童遊戲》的音樂。鮑里斯·科赫諾(Boris Kochno)寫了劇本,萊昂尼德·馬辛(Léonide Massine)編舞。在米羅看來,兒童遊戲應該是粗暴且混亂的,與甜蜜和天真的情感觀念無關。他在1932年2月23日從蒙特卡洛寫道,描述了他設計作品對觀眾的預期效果,就像是拳手的拳擊:“我對待一切都和我最近的作品一樣:幕布,第一拳擊中觀眾,就像這個夏天的畫作一樣,具有同樣的暗示和暴力。接著是一陣鞦韆、上鉤和左右肋腹的雨,整個事件——大約持續二十分鐘的一輪比賽——舞台上不斷出現、移動和被拆解的物件”(M. Rowell, ed., Joan Miró Selected Writings and Interviews, Boston, 1986, p. 119)。杜邦記錄了一個為幕布所做的研究,藝術家送給了馬辛(編號412),還有兩件其他相關作品(編號413-414)。
《兒童遊戲》的首演於1932年4月14日在蒙特卡洛舉行。這個芭蕾舞劇取得了成功,在隨後的布魯塞爾和巴黎也受到了好評;該劇團於次年將製作帶到了巴塞羅那。在巴黎表演結束後,米羅返回巴塞羅那,在7月期間,他在蒙特羅伊格的家族莊園進行了一系列小型油畫的工作,這些畫作是他回歸二維工作的標誌(Dupin,編號393-410)。受到藝術家最近與俄羅斯芭蕾舞團的經驗的啟發,這些作品中的圖像在構思上具有彈性和動感。絕對的清晰度始終是一個重要關注點;即使是在具有重疊形式的多人物構圖中,這些人物也清晰地凸顯在黑暗的背景中,就像他“反繪畫”構造中的物件一樣。
1933年1月下旬,米羅創作了一系列由從目錄、報紙廣告、技術雜誌和海報中剪切的照片和手繪插圖製作的十八幅拼貼畫,這些拼貼畫經常描繪工具和機械裝置,他將這些圖像排列並黏貼在大張紙上,而沒有進一步加入自己的手筆。在2月11日完成這組作品後,米羅於3月3日開始根據這些拼貼畫創作大型油畫,從貼在畫布上的圖像中提煉和抽象出形式,同時使用拼貼畫作為建立這些元素之間空間關係的指南。米羅在6月12日完成了這一系列作品,每幅畫對應著十八幅拼貼畫(Dupin,編號415-432)。這些畫作包含各種扁平、清晰劃定的形狀,將即使是最明確的機械源圖像進行有機的轉換,置於黑暗、多色調的畫布背景中。
從1933年8月8日到10月初,米羅還進行了一系列的繪畫拼貼,結合了剪切和黏貼的插圖與手繪(杜邦素描,編號375-398)。在1933年12月出版的超現實主義藝術期刊《牛頭怪》(Minotaure)上出現了米羅的一份聲明,他解釋道,他的作品“總是在一種幻覺的狀態下誕生,由某種觸發——無論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引起,而這是我一點也不負責任的。至於我的表達方式,我越來越努力地追求最大程度的清晰、力量和塑形攻擊性——換句話說,引起一種立即的身體感覺,然後再傳遞到靈魂中”(M. Rowell, ed., 同上,1986年,第122頁)。
米羅在1933年後期為洛埃布完成了Mural I-II-III,或許是在他的經銷商在Georges Bernheim畫廊舉辦的個展期間,也就是在十月份左右完成的,當時整個基於拼貼的十八幅畫作系列被一同展出。在11月5日,就在展覽快結束時,米羅寫信給他的紐約經銷商皮埃爾·馬蒂斯:“我想你應該已經收到了我為在Georges Bernheim畫廊舉辦的展覽所發的公告。皮埃爾(洛埃布)和我都很高興;從商業角度來說現在無法說太多(指全球大蕭條),但從士氣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皮埃爾告訴我,一旦這個展覽結束,你想在紐約組織一個展覽,這會讓我非常高興,也讓我感到非常榮幸”(引自展覽目錄,同上,1993年,第331頁)。
皮埃爾·馬蒂斯確實在1933年底給了米羅一個個人展覽,這是經銷商第二次為這位藝術家舉辦的展覽,於1934年1月中旬結束。大約四年後,米羅為皮埃爾和蒂尼·馬蒂斯的幼兒保羅、傑基和彼得繪製了一幅壁畫作品,安裝在他們的育嬰室裡(杜邦,編號596)。“畢加索非常喜歡它,並說這是我做過的最好的事情之一,”米羅給馬蒂斯寫道。“我自己也很喜歡它,但可能對你的目的來說有些戲劇性。” 這位藝術家給這幅畫作取名為《被鳥蜻蜓之過境所困擾的女人,凶兆的壞消息》,這是他對於近期簽署慕尼黑協定的回應,該協定的緩和條件迎合了希特勒的要求,導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這幅壁畫完全不是傳統的育嬰室食品,”約翰·羅素寫道。“甜蜜的夢想在其中沒有任何角色…追逐和迫害是其主題。這些人物是怪物,空間是幽閉的,恐慌無所不在。但作為1938年歐洲的肖像,它是完全正確的”(《馬蒂斯:父與子》,紐約,1999年,第129頁)。
洛埃布育嬰室壁畫的縱向格式讓人聯想到古典古代的壁飾,遠在那之前,還有史前洞穴壁畫中所呈現的錯綜複雜的圖像陣列。此外,它們還喚起了晚期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描繪狩獵場景的掛毯。米羅接下來的主要畫作是在1933年末和1934年初創作的五幅大型畫布,延伸了Mural I-II-III的裝飾理念,實際上是用作挂毯的設計(杜邦,編號459-463)。
“米羅的畫作,就像史前洞穴壁畫一樣,呈現了共同的場域中的孤立存在,而不是統一組成的協調組合,”藝術與考古學教授希德拉·斯蒂奇解釋道。“各個部分在空間中分散,不考慮比例、形狀或位置的合乎邏輯的排序。在某些地方,人物之間建立了有意義的關係,情節開始浮現。但即使在這些情況下,所暗示的活動也是模糊不清的。儘管在敘事方面可能沒有真正的統一性,但仍然存在著強大的、和諧的光環。這就是米羅如此追求捕捉的‘宗教本質,事物的魔力’。一種籠罩全身的神秘氛圍存在著……類似於史前洞穴的精神氛圍,被認為是冥想或儀式遵循的神聖場所”(《喬安·米羅:符號語言的發展》,華盛頓大學藝術畫廊展覽目錄,聖路易斯,1980年,第32頁)。
“當我們第一次看到米羅為兒童房間畫的這些畫時,它們放在G·大衛·湯普森夫婦的卧室裡,就在他們在西爾港的新房子裡。當我們在拍賣會上購買它們時,我們首先把它們掛在哈德森松樹莊園的音樂室裡,它們看起來還不錯,但我們並不經常看到它們。在建造我們在西爾港附近的新房子Ringing Point之後,我們在客廳找到了它們的理想位置。同一個房間裡還有另一幅我們早些時候購買的米羅畫作[Dupin,編號427]”(M. Potter et al.,1984年,第286頁)。
- 藝術家介紹 / Joan Miro 胡安·米羅
胡安‧米羅為20世紀其中一位最享負盛名的西班牙藝術家,在漫長及豐碩的創作生涯裡,他一直熱衷於演繹日常物品及發掘它們內在的詩情畫意。他畢生的抱負是將藝術與生活連繫起來,憑著他獨特的洞察力,他從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物品中找到具詩意的特質。
米羅筆下的星星月亮太陽,一個個抽象符號,被認為是抽象畫的經典,也是他最著名的繪畫風格,但其實米羅深受立體派、超現實主義,甚至達達主義的影響,畫風多變。他決心要將詩畫合而為一,要革新繪畫這種傳統藝術媒界,甚至曾說過:「我要刺殺繪畫!」
米羅曾與超現實畫派關係密切,這些超現實主義者態度開放,也擅用不同媒界創作,一直在嘗試融合詩畫二事,米羅曾將一首詩拆開,成為他繪畫的題目,又嘗試在畫裡表達他的詩意性,米羅的畫雖然被認為是抽象畫,但很多時候他筆下繪畫的都是符號,而從符號之中,大概可見到它是星星、月亮,或是一隻小狗/動物。比較起全抽象繪畫,它們更見到米羅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他曾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還有一次西班牙內戰,那年代再見證特權階級統治,他是因為避難,才在鄉間居住,在沙灘裡仰望星空,啟發了他繪畫星座系列(Constellations,1940-1941)。及後他開始用星星月亮太陽來作畫,而星座系列成了他的標誌性語言。」談到他受的藝術影響,羅館長說米羅大約在三十歲到了巴黎,當年巴黎是世界最前衛的藝術中心,各個畫派百家爭鳴,他除了較受到影響的其實超現實主義,還有達達主義和立體派,「據他自言,他會從每個畫派之中學習,但他不承認自己屬於任何一個畫派。」
刺殺繪畫
米羅生前曾說過,自己「越來越重視在作品中使用的物料,為了讓觀眾作出反應前就感受到衝擊,我覺得一種豐富而有力的材料是必要的。這樣,詩意就透過塑造的媒介表現出來。」他本來使用的物料就具顛覆性了,他會使用木材、聚合纖維板、黃銅板、砂紙、瀝青等做創作,在上面刮擦、鑿孔、黏貼、拼貼,各適其式,也許對米羅有基本認識的人來說,看是次展覽,比較驚奇的是原來他有這麼深受達達主義影響,例如就在入口處展出他在1933年繪畫的油畫(此作就簡單的叫《Painting》),這畫的起源,是他喜愛收集雜誌,然後在雜誌上剪下不同的「物件」,拼貼成作品。展覽既有展出他當初的拼貼,又有展出他後來再演化成了的油畫作品。大家都知道,拼貼和現成物(Ready Made)都是達達主義的慣技,米羅只是信手拈來,作為他的習作。
米羅為何偉大
米羅為何偉大,能與畢卡索、達利比肩?他又與其餘二人有何不同?「有人稱米羅為超現實主義畫家,一般都說它創作的是抽象藝術,因為大家都很難用一個主義去定義他,他的兼容性很強,這是他跟畢卡索、達利很不同之處。提起畢卡索多想起立體主義,達利多想起超現實主義。另外,米羅也強調回歸自然,無論他身在繁華的巴黎,或在那裡,他每年都會抽出兩個月,回到加泰隆尼亞的鄉間,從自然中得到力量。」她說:「米羅好認真的對待不同媒界,跟不同年代的藝術家合作,他喜歡民間藝術,也和手工藝的師傅合作,創作度很廣泛,創作期橫跨六十年,相當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