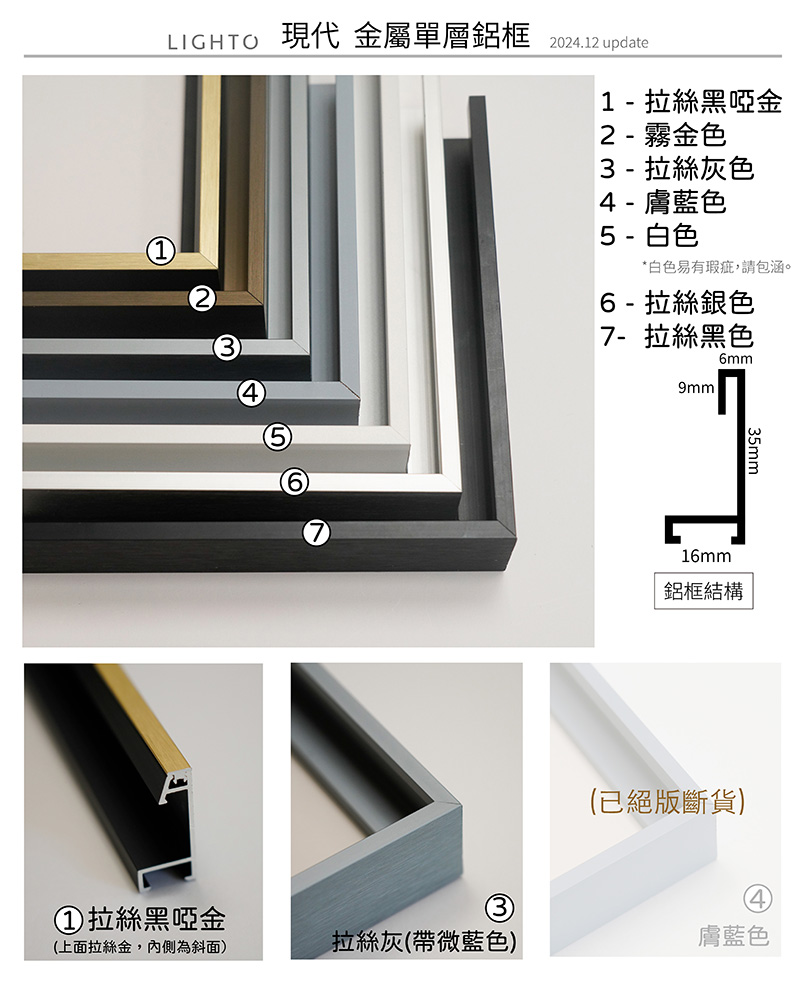--- 輸出相紙: 藝術微噴 雪面藝術紙
*單買相紙:3-5個工作日出貨。
*裱褙工法耗時費工,訂單需等候 2-3週,請耐心等候。
懸掛方式:
鋁框背面均有鋼索,可於牆上黏貼3M無痕掛勾(請購買5kg以上版本以策安全)即可懸掛。
- 作品名稱 / Homme et femme 男人和女人
尺寸:85.3 x 60 cm
作品年代:1935
- 實拍作品 x 銀色鋁框
這幅畫中的男女人物或許可追溯到一個古老的故事:一位輕率的年輕人匆忙離開一位受到嚴重冒犯的女士,或者更具體地說,一位悲傷的母親在責罵自己任性的兒子。米羅賦予這個場景流暢的手勢線條,融合了匆忙斑駁的油彩,這種風格正如同壁畫上常見的,甚至是最古老的那種——米羅親身研究過和閱讀過加泰羅尼亞嶙峋地形深處洞穴壁畫中那些史前的圖案,這些洞穴位於最後一次冰河時期的周邊。然而,這個場景更重要的是一幅來自當代日常生活的諷刺畫,可能是米羅在巴塞羅那街頭親眼目睹的平凡遭遇。然而,它的最終意義不僅僅是軼事性的;米羅實際上暗指的當天事件更加深刻和潛在危險。
在《Homme et femme》中,人物的流暢輪廓似乎是由手中輕巧的筆以近乎連續的阿拉伯式曲線繪製而成,就像在粉刷的室外牆壁上一般,為他塑造了陽具形狀,而為她則呈現出陰部的符號。深紅和金色的色帶暗示著她代表著西班牙母性,甚至是整個國家本身,而紅色和黑色的顏色可能顯示他尚未決定向共產主義左派還是法蘭哥主義右派宣示效忠;無論哪種情況,她都在全力斥責他。我們聽到米羅以她的聲音高聲呼喊,“西班牙,要小心!”
- 藝術家介紹 / Joan Miro 胡安·米羅
胡安‧米羅為20世紀其中一位最享負盛名的西班牙藝術家,在漫長及豐碩的創作生涯裡,他一直熱衷於演繹日常物品及發掘它們內在的詩情畫意。他畢生的抱負是將藝術與生活連繫起來,憑著他獨特的洞察力,他從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物品中找到具詩意的特質。
米羅筆下的星星月亮太陽,一個個抽象符號,被認為是抽象畫的經典,也是他最著名的繪畫風格,但其實米羅深受立體派、超現實主義,甚至達達主義的影響,畫風多變。他決心要將詩畫合而為一,要革新繪畫這種傳統藝術媒界,甚至曾說過:「我要刺殺繪畫!」
米羅曾與超現實畫派關係密切,這些超現實主義者態度開放,也擅用不同媒界創作,一直在嘗試融合詩畫二事,米羅曾將一首詩拆開,成為他繪畫的題目,又嘗試在畫裡表達他的詩意性,米羅的畫雖然被認為是抽象畫,但很多時候他筆下繪畫的都是符號,而從符號之中,大概可見到它是星星、月亮,或是一隻小狗/動物。比較起全抽象繪畫,它們更見到米羅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他曾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還有一次西班牙內戰,那年代再見證特權階級統治,他是因為避難,才在鄉間居住,在沙灘裡仰望星空,啟發了他繪畫星座系列(Constellations,1940-1941)。及後他開始用星星月亮太陽來作畫,而星座系列成了他的標誌性語言。」談到他受的藝術影響,羅館長說米羅大約在三十歲到了巴黎,當年巴黎是世界最前衛的藝術中心,各個畫派百家爭鳴,他除了較受到影響的其實超現實主義,還有達達主義和立體派,「據他自言,他會從每個畫派之中學習,但他不承認自己屬於任何一個畫派。」
刺殺繪畫
米羅生前曾說過,自己「越來越重視在作品中使用的物料,為了讓觀眾作出反應前就感受到衝擊,我覺得一種豐富而有力的材料是必要的。這樣,詩意就透過塑造的媒介表現出來。」他本來使用的物料就具顛覆性了,他會使用木材、聚合纖維板、黃銅板、砂紙、瀝青等做創作,在上面刮擦、鑿孔、黏貼、拼貼,各適其式,也許對米羅有基本認識的人來說,看是次展覽,比較驚奇的是原來他有這麼深受達達主義影響,例如就在入口處展出他在1933年繪畫的油畫(此作就簡單的叫《Painting》),這畫的起源,是他喜愛收集雜誌,然後在雜誌上剪下不同的「物件」,拼貼成作品。展覽既有展出他當初的拼貼,又有展出他後來再演化成了的油畫作品。大家都知道,拼貼和現成物(Ready Made)都是達達主義的慣技,米羅只是信手拈來,作為他的習作。
米羅為何偉大
米羅為何偉大,能與畢卡索、達利比肩?他又與其餘二人有何不同?「有人稱米羅為超現實主義畫家,一般都說它創作的是抽象藝術,因為大家都很難用一個主義去定義他,他的兼容性很強,這是他跟畢卡索、達利很不同之處。提起畢卡索多想起立體主義,達利多想起超現實主義。另外,米羅也強調回歸自然,無論他身在繁華的巴黎,或在那裡,他每年都會抽出兩個月,回到加泰隆尼亞的鄉間,從自然中得到力量。」她說:「米羅好認真的對待不同媒界,跟不同年代的藝術家合作,他喜歡民間藝術,也和手工藝的師傅合作,創作度很廣泛,創作期橫跨六十年,相當難得。」